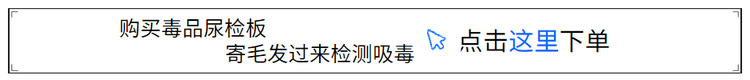
要弄明白他们为什么抽大麻,就要先了解大麻的历史。大麻原产于亚洲中部,最早于六千多年前在中国有大量种植。大麻是有多种用途的高价值作物,除了萃取瘾品之外,产品包括食用油、可食用的大麻籽、牲口饲料、大麻纤维。中国人用大麻纤维制作绳索、渔网,以及平民大众的衣服原料——因为丝织品只有富贵人家穿得起。

由于大麻的用途广,韧性强——在各种气候区从海平面到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度都可以栽种,所以必然会成为广泛栽种的作物。大麻刺激精神的作用在许多社会中受到重视,其中又以印度为最。
印度被称为世界上最早崇尚使用大麻的文化。昔日的印度教医学(ayurvedic)与伊斯兰教医学(tibbi)的诊病者会开出口服大麻的药方来治疟疾等传染病或风湿等疼痛症。一般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民间疗法也使用大麻,并且用它来消除烦躁与疲劳,在收获季节尤其常用。战士们饮大麻药来壮胆,苦修僧借它来安神;新婚夫妇用它增进情趣。大麻也是廉价而普遍的春药,甚至可在母马交配前喂食大麻。
大麻在印度的普遍使用显然在莫卧儿王朝统治的时代(1526~1857年)达到顶峰,印度次大陆上处处有人种植大麻,也到处盛行使用各种不同的大麻配方药剂。英国人占领印度以后,认为大麻是麻醉剂而反对使用。到了20世纪,西化的印度统治阶级也加以反对。一般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看法大都容忍效用温和的大麻药,毕竟三教九流各行各业都有人服用。至于吸食大麻烟与大麻脂,令人联想到社会底层的不法之徒,所以越来越不被接受。
大麻最初在欧洲出现是什么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但很可能是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引进的。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撰写的《历史》之中有一段描写斯基泰人(scythians)在燃烧大麻籽的浓烟中“快活地叫嚣……他们以此取代普通的沐浴,却从不洗澡”。阿拉伯人从希腊医学和植物学中认识了大麻,也在跟伊朗与印度的交易中更直接地学会用大麻。按民间传说,药用大麻于6世纪中叶传入伊朗,乃是一位印度朝圣者带来的。但有些学者认为,大麻传入近东的时间应该更早,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和阿拉姆语的译本之中都提到了大麻。
到了14世纪,大麻烟的生产已经十分稳定,在尼罗河三角洲尤其显著。这期间,阿拉伯贸易商已经把大麻一路传播到非洲东海岸,再由此传入非洲大陆的中部与南部地区。简言之,哥伦布率领三艘缠满大麻绳索的大船于1492年8月3日早上从西班牙起航之前,大麻烟已经传遍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地区了。
西班牙人于16世纪开始在殖民地栽种大麻,一直到大麻农业在加州兴盛了一段时期的19世纪早期为止。法国人和英国人也在殖民地种大麻。殖民列强种大麻为的是收取大麻纤维,主要是供船舰的绳缆之用,从未重视大麻的药用价值与影响精神状态的效能。
列强引入的奴工的看法可就不一样了。来自安哥拉的奴隶把(用朗姆酒、劣等烟草和其他东西买来的)大麻带到巴西东北部的甘蔗园,大约在1549年以后成为固定种植的作物。按传说,奴隶们把大麻籽放在捆入破烂包袱的布娃娃里。地主准许奴隶在一行行甘蔗之间的空隙栽培maconha(即大麻),也准许他们在农忙以外的闲暇时间抽大麻做白日梦。地主们自己却依然只抽雪茄。
当地的印第安人以及欧洲人与印第安人混血的乡下人学会拿大麻当药材和联络感情之用,后来城市的劳工也学会了。人类学家薇拉·鲁宾(Vera rubin)称这种使用模式为“大麻情结”,用途包括绳索与衣着、食物与香料、提神剂与补品、药材与消遣解闷之物(这末一项大多是在男性欢聚的场合中)。鲁宾指出:“民间对于大麻经常性的多方面使用,大致限于农民、渔民、城乡的工匠及粗重劳工等社会底层。此外只有在宗教仪式中有神职人员使用。”
欧、亚、非洲的大麻情结也在巴西发生,大麻变成巴西殖民地区穷人的鸦片。北美洲的大麻种植虽然比南美洲普遍,收成也比南美洲好,却没有出现这种模式。极有可能是因为运往英国殖民地的奴隶来自更靠近西非海岸的一带,使用大麻的风气并不盛行。此外,欧洲来的殖民者本来就有自己的以酒解闷的文化,以及17世纪兴起的抽烟消遣的文化。
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这段时间,美洲的大麻烟重心从巴西移到了加勒比海地区。转移过程与吸鸦片的全球化发展类似,关键因素都是移民与远途运输。自1838年起,美洲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结束,甘蔗园面临欠缺廉价劳工的问题。殖民农庄主人便从印度输入契约佣工,其中将近50万人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大麻情结也跟着他们一起到来,这一点颇令白人社会不满。1913年的牙买加 《拾穗日报》 (Daily Gleaner)的社论指出,这东西传到有非裔族群的岛上,成为非裔族群喜欢栽种的作物,这是不好的现象,日后可能发生和中国的鸦片问题差不多的祸害。
事实果然与这个预言相去不远。到了1970年代,牙买加乡村男性成年人口有60%抽大麻,其中半数烟瘾很大。用大麻泡茶或充当补品与提神剂的民间药用方式也十分普遍,甚至笃信基督教的人也不认为吃喝大麻剂是坏事或可鄙的。
1900年以后的30年中,有超过100万名的墨西哥劳工进入美国西南部,吸大麻烟的习俗也跟着他们进入美国本土。当时正在进行的香烟革命教美国人用肺来吸入瘾品,顺便带动了大麻烟的传播,美国境内充裕的大麻供应量是另一股助力。田纳西州的罪犯只需摘起在路旁发现的大麻的花冠晒干,就有大麻烟可抽。圣昆丁监狱的受刑人索性就在狱内的空地上种起自用的大麻。
因为普遍容易取得,大麻烟的价格低廉,一支售价在5~50美分之间。这是认同此种新兴流行亚文化的都市年轻黑人负担得起的价钱。这种亚文化的英雄人物是爵士乐手,他们以身作则抽大麻而居推广之功。
劳工阶级男性利用大麻逃避现实、及时行乐也不算新鲜事。但当时美国人服食的大麻和传统印度大麻的服用形态并不一样,这是比较限于满足快感需求的,并不当作药用茶或民间药剂,只图吸它能够享受一下。美国人的使用模式有别于古老的且用途较多样的大麻情结,鲁宾称之为Marijuana complex(大麻烟情结)。
美国的大麻情结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跻身主流社会。自从19世纪40年代巴黎的“大麻会馆”进入全盛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就开始抽大麻,为的是寻找新鲜刺激以及诗人波德莱尔所说的“强化的个人特质”。但带头做的人非常少,跟进的人也寥寥无几。到了1960年代,数以百万计的穿着喇叭裤的学生点起大麻烟,情况可就不同了。心理学家威廉·麦格劳特林(William McGlothlin)对这个现象做了简单扼要的概括:“透过嬉皮运动的中介,大麻烟从一个社会底层的瘾品脱胎而成为中等阶级与上流社会的瘾品。”媒体对于嬉皮有利的(即便不是故意偏袒,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报道,加上种族隔离制度、都市物质主义、越战的令人反感,都引起年轻人一窝蜂地效尤。大麻烟正好成为叛逆行为的多重价值的象征,因而在高中生及大学生之中蔚为风潮。根据密歇根大学的研究报告,从大一到大四的吸大麻人数是逐年上升的,但研究生的吸食者递减。因为研究生比较偏好镇静剂。
后起的这个大麻情结在美国特别受瞩目。据估计,到1979年为止,约有5500万美国人吸食过某种形态的大麻,其中2/3是18至20岁的年轻人。类似现象很快就蔓延到全世界。典型的吸食者是十几岁到20出头的没有虔诚宗教信仰的男学生。大都市和市区近郊是主要的市场所在。丹麦的大麻吸食者最常出没的地方是哥本哈根,瑞典吸食者的集中地是斯德哥尔摩,其他国家可以类推。不论在哪里,年轻的大麻吸食者进而吸食其他瘾品的可能性都远高于不吸大麻的人。
由于年轻人对于瘾品引起的不良反应的忍受力比较强,自然就比年长的人更想要寻求新鲜刺激,更容易瞻前不顾后,也更急于模仿同侪。这些心理特性都易于促成瘾品滥用。在生活富裕的西方社会以及正在西方化的社会里,在凸显个人风格、及时行乐、性解放的意识正在抬头的时代,这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尤其不可忽视。
传播媒体从旁煽风点火也是功不可没的。以1955至1972年间美国与欧洲发行的电影计算,有72部含有与毒品相关的剧情或主题。电视的新闻和娱乐节目也都在告诉观众最新的瘾品的使用方式,而播放的广告更不断鼓吹毫无限度满足个人欲望的观念。克里斯托弗·勒希(christopher Lasch)曾经指出,“舒利兹”啤酒当年广告中那种偏颇言语根本与啤酒无关,推销的其实是唯我主义:“你只走这一遭人生,能享受的玩意儿,一样也别放过。”年轻人越认为自己是不吃白不吃的消费者,越生活在自我满足与失望循环的世界里,就越有可能认为大麻只是一大堆商业推销的快感之中的一项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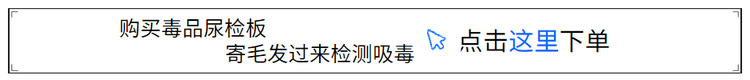

文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