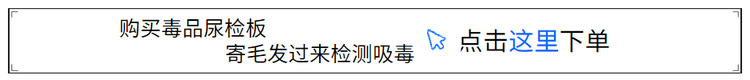
喀布尔毒品迷局:死于30美分
在阿富汗这个制造了全球94%的海洛因的国家,一小包海洛因只要30美分。喀布尔支离破碎的市政文化中心是数干名阿富汗毒品受害者的栖身之所,已处于吸毒“生涯”最后一个阶段的绝望“永久居民”们,正聚集在这个像死亡集中营的建筑的阴影与角落里,用注射或吸食海洛因的方式挥霍着自己的生命……
漫步喀布尔市中心,随时都可能遭遇一群群的“活死人”。在这群“活死人”的身边,喀布尔这座城市正在以异常缓慢的速度从战乱中复苏。经过近30年的狂轰滥炸,喀布尔市政文化中心这座久已废弃的巨大建筑已经摇摇欲坠。
占领了市政文化中心主建筑的“活死人”数量大约为2000人,他们每天聚集在一方屋檐下,或者说是在类似于屋檐的遮盖下熬过漫长的黑夜,等待黎明。他们躺着的地方堆满了注射器、针头、垃圾以及他们自己的排泄物…
这就是经历了战火洗礼的阿富汗的新面孔,以及这副新面孔最阴暗的一面。自从阿富汗正式宣布“被解放”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7年时间,这个国家却一直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这个…家拥有至少10万因反步兵地雷而缺胳膊断腿的残疾人;这里的腐败现象也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更顽固、更泛滥;有人约46%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70%的国民是文盲;在阿富汗的东南部,还有大约30%的国土仍然处于塔利班的控制之下。此外,阿富汗的国土还被赋予一项异常独特的功能:大约15.7万公顷的土地被用来种植罂粟,全球海洛因总量的94%,都来自这个同家的耕地。阿富汗是18万深度吸毒者的家园,这其中包括3万名妇女。他们每年消费掉的毒品可达100吨!
消费群落
前喀布尔市政文化中心就是阿富汗贩毒产业最符合逻辑的产物。这是一个半独立、半封闭的“群落”,所有的日常供给与日常消费都在封闭的围墙之内解决,从而与围墙之外的喀布尔城市生活彻底隔绝开来。在这里,“消费者”和“经销商”(通常不久之后也成为“消费者”)挤在一起。那些“消费者”无论是未成年人还是上了年纪的人,都是身体极度虚弱,在烟雾缭绕的阴暗房间中或在漆黑的地下室中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然后,围绕在这片“人体沼泽”周边的“经销商”便开始游走,兜售包装在锡纸中的茶色粉末、新的或二手的注射器、细长的纤维引火物……除了毒品,面包、水和瓶装果汁则是小贩们经常兜售的商品。他们在那些虚弱的躯体间来回走动,大声叫卖,仿佛他们正身处一个繁忙的火车站。
在这座建筑物中,瘾君子们可以找到任何生存所需要的东西——也可以找到那些让他们的生命毁灭的东西。一剂海洛因在这里只需要25到50阿富汗尼,这大抵相当于0.35欧元至0.7欧元。这样的毒品价格即使在这个月平均工资仅为100美元的国家也不算高。在喀布尔的大街上,乞丐们平均每天也可以乞讨到大约两欧元。
对于很多瘾君子来说,他们的故事都是相同的。他们在相对清醒的时候会告诉你:他们虽然是阿富汗人,却来自阿富汗周边的几个国家。在局势最动荡的时候,他们从自己的国家以难民身份来到阿富汗,平时靠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其中大部分人都在靠近边境地区的大理石采石场里做苦力。几个星期后,他们就会因肌肉疼痛和疲劳而无法再干下去。这个时候,采石场的工头就在采石场矿场主的默许下让他们吸食海洛因,以此来减轻因过度疲劳而带来的伤痛。
在最初的“治疗”持续一段时间后就不再有免费的海洛因,但劳工们已经开始对毒品上瘾,而黑心矿场主从此就不必再向劳工们付钱,而开始用海洛因代替现金支付劳动报酬。这对矿场主们来说有一个巨大的好处:除了更加节约“成本”之外,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劳工们的劳力会更加充沛——他们甚至因感觉不到疲劳而不分昼夜地工作,直到那个“折返点”。随着劳工们吸食毒品的剂量越来越大,他们早晚会从一群劳动力变成一个个垂死挣扎的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随后,矿场主会用一批新的难民取代之前的劳工,工头则会将之前的这批劳工驱逐出采石场。有时甚至会借助警方的力量来驱逐,理由就是非法移民——因为这些难民都没有护照。没有护照,没有钱,也没有健康的身体,无法再回到自己的祖国,喀布尔的市政文化中心就此成为他们惟一的选择。
绝望城市
在这些“活死人”中,也有着另外一种类型的故事,但更加肮脏,也更加令人绝望。这类故事都有一个中心思想:在一个毒品比面包还要便宜的国家,被毒品攫取灵魂实在是再寻常不过的一件事情。卡西姆·诺里伊独自一人坐在市政文化中心的一个房间中吸食海洛因。这个27岁的年轻人有着运动员一般强壮的肌肉,体形看上去就像是一具雕塑作品,脸庞看上去则像一个模特。其实就在几个月之前,他还是一位运动健将,曾经在2008年伊朗国际跆拳道锦标赛中获得过银牌。“当时我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我们国家的骄傲……”但现在他坐在一堆排泄物之中用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直白方式叙述他的遭遇,“我因为和朋友开了一次玩笑而开始吸食毒品……但是今天,我什么事情都干不了了,现在我整天都活在羞愧与耻辱中。”
在喀布尔,警方也会时不时对大楼进行清剿。通常情况下,一到两位警官会冲进大楼捏着鼻子缴获少量毒品,用他们的警棍随机殴打几个不幸恰巧没有体力逃跑的瘾君子,然后将剩下的没有体力逃跑却有体力走动的瘾君子驱赶出大楼。后者被驱赶出大楼后就在院子里傻傻地站着。当警察离开以后,他们马上就可以重新回到大楼里。
一个毒贩这样抱怨那些来自距离大楼只有几百米的喀布尔3号警察局的警官:“他们全都腐败了!”他嚷嚷着,“他们洗劫我们,端着冲锋枪,他们威胁要将我们送进监狱。但他们只不过是要从我们身上勒索钱财,让我们用钱来换贩卖毒品的自由!”
这样的叙述或者有些夸张,但也同样无比接近现实。
国民经济支柱
“更不幸的是,毒品经济已经成为阿富汗整体经济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反麻醉剂管理局负责战略沟通的哈鲁恩·拉希德·谢尔扎德说:“情况可能还要更糟糕,自2003年以来,阿富汗每年播撒的罂粟种子都在逐年攀升,鸦片产量也一直稳步上升,目前已经达到每年5000吨的产量。而2011年,阿富汗也首次在全国34个省均发现有罂粟被种植和收获,农村人口总数的14%参与到罂粟的种植之中。因为种植罂粟能获得比种植普通作物高出四倍的收入。如今,阿富汗仅鸦片一项的总体收入就可以达到30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占到了这个国家仅为130亿美元的年国民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
即使自2004年以来一直担任阿富汗总统的哈米德·卡尔扎伊,也因为牵扯数宗贩卖毒品丑闻而声誉受损,这其中最严重的一起案件甚至牵扯到了他的兄弟阿赫迈德·瓦里。有消息人士指出,这位阿富汗总统的亲兄弟很有可能就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毒品贩子之一。从政治的角度看,毒品也让卡尔扎伊“颇有斩获”——他已经与众多阿富汗毒枭和军阀达成妥协,这其中就包括阿富汗副总统穆罕默德·法西姆——此人简直就是脖子上挂着牌子的毒枭。
阿富汗之所以是今天这样的局面,罪魁祸首很大程度上就是今天的“国际社会”。2002年,因穆拉赫·奥马尔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权和连年内战的荼毒,阿富汗国民经济已经陷入崩溃的边缘。阿富汗人原本期待国际社会在对阿富汗进行狂轰滥炸之后会参与阿富汗国家社会的重建,谁知这样的指望最终落空。假如当时国际社会对阿富汗重建的援助及时而到位,毫无疑问将获得阿富汗社会整体的认同,塔利班控制的土地也将被收复,各地军阀的权力也将被削弱,这样如今用土地种植罂粟的农民就会拥有更好的选择,阿富汗也就不会沦落到成为全球海洛因第一输出国的地步。但国际社会放弃了阿富汗。他们先是轰炸阿富汗,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样的政策最终让塔利班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并得以重新武装起来,以更加强悍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让这个国家的国民依然对其充满敬畏。至于那些军阀,他们依然控制着这片土地,从这个国家空前的混乱中汲取营养,积蓄力量。
在谈到阿富汗重建前景时,曾参与北约对阿富汗战争的意大利公共情报官马尔可·阿莫里耶罗中校说:“在这里,大多数农民都被塔利班或当地军阀逼迫着种植罂粟。不过.我们已经试图说服一些曾经种植罂粟的农民改种藏红花,虽然他们仍然担心遭到塔利班的报复。藏红花在欧洲的售价较高,因此能够获得比种植罂粟更加丰厚的收益,但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保护这些农民。为了稳定局势,我们必须增加战争预算。不过,我们现在在预算上的投入与需求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另外一根“九牛一毛”是联合国开发公司UNDC于2011年5月份在喀布尔倡导创立的引导戒毒中心。由一家位于喀布尔大学附近被炸成半废墟状态的工厂改建而成,因为资金严重不足,条件极其恶劣,包括志愿者、心理学家、服务人员及医生在内的不过50人左右。
但负责戒毒项目的瓦利德·尤拉赫说,“与几个月前政府漠不关心的态度相比较,戒毒中心的成立已经算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这为阿富汗的社会复兴带来了一丝曙光。但是,这丝曙光确实太微弱了,而且还不知能亮多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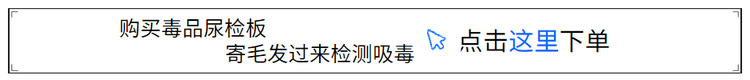

文章评论